
赵轶峰
历史学意识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既已凝重,其体现于史学形态,自然复杂多样。约略言之,可得数端。
官史学传统为贯穿始终之特色
不晚于商周时代,国家机关的历史记载活动已经制度化。当时史官所司,为记载当下发生之事,记录过于事后书写、编纂。刘知幾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并称,汉武帝时“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唐初,“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史官时,其职能已较古时有所扩展,文献、记述、修纂兼而领之,又兼天文、日历之事。故《史记》虽为个人所修,然而非为史官,其事难成。后世史官,皆为常设,史馆因事而设。就明代言之,翰林院官即为史职,身居清要,玉堂金马,为大学士进身之阶。
官史学固极发达,又与私人修史并行
孔子之前,周王室暨各诸侯国,皆有官方史书。其时私人是否可以著史,不得而知。可确知者,孔子所为并非延续前代史官之事,而是私人修纂史书。孔子以水边林下之人,取官修史书而删订之,“笔则笔,削则削”,可知私人修史,并非禁忌。所成之书,举世以为经典,传注解说,随之而起,于是史学成天下公器。以私人而言天下既往之事,纵横驰骋,内容固以庙堂经验教训为主,然而已非当下记录,要在贯通,意在载道。故孟子称其书,“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后私人著史,累累相因,数量远在官修史书之上。私人修史,实际构成民间思想文化一大空间。
编年史完备,为中国传统史学另一独到之处
孔子之前,史籍体裁已非一端,记言、记事,各有其传。然而孔子于各种可能之间,独取编年,所作《春秋》,为后世史书一大宗本。不仅诸编年史如《资治通鉴》之类直承《春秋》,即使纪传体通体、断代史,分本纪、传、志言之,仍取编年次第。后世实录亦非当时记录,而为皇帝去世之后方始编纂之史书,兼有保存文献、记述经验与评价功能。纪事本末体,就以事为章言,异于通体编年之史,然而叙事之法仍取时间次第,不脱编年根基。刘知幾论编年体之长:“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此种编年史,为发达水平史学体裁,与罗宾·乔治·柯林伍德所谓罗列事件而无思想,“剪刀加浆糊”式之编年史,以及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作为历史之尸体的编年史皆有根本不同。刘家和先生曾就中西编年史根本差异作专文讨论,事理已明。
纪传体史书为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独到建树
纪传体之长,要在分类纵横,交错呼应,功能最为周备。刘知幾称:“《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现代史学兴起之后,问题研究成为主流,历史编纂学已然转向,故今人欲知一代史事,眼花缭乱,多难采择。所谓史学“碎片化”,实非晚近注重社会史、微观史所致,由历史编纂学言之,乃现代史学之初,即发其端。
编纂学发达为中国传统史学一大特色
古人编纂史书,固以国家政治、显著人物行迹为主,于现代社会而言,局限在所难免。然而体裁之长,不可因古人见识局限而予忽视。今人若拟作一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周备之史,仍可参酌损益。其体有长于目下流行大多数史书体裁者,可以断言。编年、纪传各具短长,相得乃彰,是以中国古人二者并存,且于二体之外,不断创新。刘知幾称:“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各家纷纭,诸体繁多,并非古人无事生非,要在诸体各有所长。孔子即曾有言:“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因不以任何一家、一体为尽善,得代有出新。
史学因轴心期觉醒而确立基本地位,因《春秋》《史记》而确立编纂学传统,官私竞相治史,形成普遍文化,遂成历代赓续编纂史书之传统
此一现象亦为中国传统史学所独有。《史记》之后,历代史书,断代多于通史。究其缘由,乃因将前人纂史与今人纂史视为同一事业,不欲使之断裂,亦不轻言颠覆。故若前史过简,后人为之传注;有阙遗者,后有增补;有散佚者,后有辑佚;有舛误者,后有校勘。诸凡一代之史,虽皆以王朝统治为中心,然而内容远超政治范围。食货关系经济民生,天文关系信仰、科技,地理、沟渠/河渠关系水系、水利,礼于制度之外关系文化,艺文关系学术、艺术。故中国古人著史固为政治教训,亦为提点一代知识境界,若以帝王将相家谱视之,不免偏颇。
著史于文化、社会体系中居如此崇高地位,从业既多,历代赓续、创新,成就历史编纂学之发达
如史学史家言历代史书,多举“史书三体”,然而古人著史固不限于三体。刘知幾于“正史”之外,仅“杂述”之书,即列出10类。刘知幾未及论而更为显著者,为历代政书。唐杜佑《通典》,启于上古,迄唐中叶,分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就内容线索而言,其书类似今人所说专门史,即国家制度史。就时间范围而言,为古今通史。宋郑樵《通志》,融合纪传、谱、略各体裁,综括上古迄于当时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就时间范围而言,亦为通史。而其综揽广阔,就内容而言,略当综合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本于《通典》,分门别类之下,详述沿革,多录原文,且兼存异说,加以折衷。三书合称“三通”,后代续编,成“十通”之数。前三通体裁并非严格一致,后续体裁各依所续,目录分类,通列史部。与唐以后文化重回大一统格局后再次整合相关,唐朝对前代制度发明择善而从,如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等等。与此相应,唐朝注重法律、制度体系文本编纂,所制《唐律》,精神暨文本形态延续至于明清。此后又有会典编纂,作为法典体系组成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后世,则为史书。此类典籍,实际融立法与存史为一体。就此而言,中国历史著作,并非皆由历史学家编纂。人类历史上著史与国家施政暨社会事务之融合,别无如此之深切著明者。
前述种种,仅取数端,远不能涵盖中国传统史学形态之全貌,如谱牒、方志当作专论。凡研治中国史学史学者,于此无不可以连篇累牍,开举多端。传统史学含诸多缺陷,无可讳言。此处要点在于,前述复杂、持续之史学形态绝不可能在以著史为政治家借题发挥或文人自我表现之事文化氛围中形成,以史学为理解人类事务根本知识构成一种文化意蕴。历史学并非任何文化系统独有之事,其得失亦非欧洲19世纪史学可以囊括。今史学理论家探求创新为应有之义,然而若言历史学整体“转向”,还需考虑历史学范围、体量、形态,三思而行。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
阅读链接
何谓“史书三体”
在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裁中,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被称为“史书三体”(亦称“史籍三体”“史学三体”)。采用这三种史书体裁编纂的史书,在传统史籍当中占据绝对主导性地位。
纪传体史书又称“正史”。纪传体的创立者是司马迁,所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体史书包含四种基本体例,分别为本纪、列传、志、表。
编年体是传统史学最古老的史书体裁。由于“秦火”之缘故,孔子编修的《春秋》成为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代表了传统史学编年叙事的最高成就。
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三体”中最晚出者。南宋袁枢改编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的主要优点可以概括为:一是选事设目自由,灵活度大;二是叙事明晰,故事化;三是叙事首尾详备,突出了事件的完整性。当然,纪事本末体也有保存史料不够和事件孤立叙述的缺陷。(董瑚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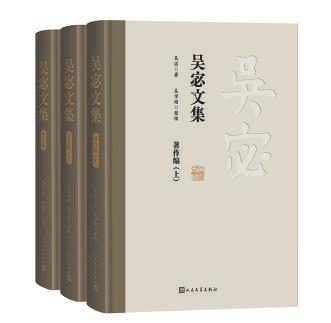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