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应帝王 汉初,政治五大支柱,韩信立“兵法”,萧何制“律令”,张苍定“章程”,叔孙通行“礼仪”,陆贾《新语》。 除了汉承秦制,也开始有了秦汉分水岭。 其时,儒术与秦制并立,缘起于汉高祖,自祭孔始,到定朝仪、作《新语》,皆由其支持,且应用于汉家政治。 刘邦对儒术的认识,从实践中来,辩士随何曾被他骂为腐儒,随何反驳:我说服淮南,使陛下如愿,岂不胜于千军万马?你见过有这样能打天下的腐儒吗?刘邦要废太子,太傅叔孙通说:太子为天下根本,本一动摇,天下就会震动。一向圆滑的叔孙通,竟不惜以“以颈血汙地”保太子,刘邦无奈,便说“吾听公”。此举,不但震撼刘邦,亦令太子敬惧,让帝王体验了儒学的道德力量。 文景之世行黄老之术,却以王道名义,班固赞曰“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故武帝一即位,孔家店就开张。 建元元年,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同时,准丞相赵绾奏,罢免那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虽未提及黄老,但明绌申商,已表明对黄老的态度,只等窦太后去世。不久,窦太后反击,孔家店关闭,直到窦太后去世,孔家店方才重启。 于是,武帝又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表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这一次,他为自己受命,准备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是从天问到人,所以,叫做“天人三问”,对此三问的回答,便是“天人三策”,帝要“究天人之际”。 首问,以大、小问,大则“从上古之治道到受命之天道”,小则从个人的性情到个体命运,“问因何可以天人相应”?次问,以无为有为问,问虞舜无为而天下平,文王有为以至于日不暇食,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三问,以天人古今问,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 此三问,见于《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答以“天人三策”。帝羡唐、虞之世,“画象而民不犯”,“成康刑错而不用”。然而,怎样才能“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呢?儒者“咸以书对”。于是,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起而应答之。 以此三问,可见武帝思想已然成熟,少年天子向着思想者王迈进了。他提出的问题,已超越了汉家制度安排的权界,不再局限于“君君臣臣”那一套既定的规范,而是从根本上反思,回到天人之际的原始立场发问,这一问,就问向国家正当性来源了。 天人三问,问向治道和天道统一性,若放在西方政治学框架里,那也就是国家法与自然法的关系问题;帝曰:何以舜无为而治,文王则有为?无为即用自然法,有为则用国家法;如何能使尧舜和文武为一,在王朝中国基础上,重建文化中国理想?在汉家天下里,如何实现两个中国——天国与人国、古国与今国融合? 自三代至秦汉,文化中国与王朝中相结合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禹汤之时到殷墟时期,通过国家与革命的方式,在文化中国之域,确立专制王权,建立世袭王朝,实现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第一次结合;第二个阶段,从汤武革命到周孔之教,文化中国与周制相结合,以宗法制齐家,以封建制治国,以民本主义及其革命理想平天下,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文化格局里,国家观念及其制度安排,属于王朝中国,民本主义天下观及其革命理想,属于文化中国,孔子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总结。 如果说孔子“吾从周”是因为周公实现了文化中国与周制的结合,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周礼文化,那么自秦汉以来,周制式微已久,秦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排斥文化中国,以“焚书坑儒”开劫,打了文化中国的劫,然其结果却是劫尽而秦亡。 汉承秦制,接着做皇帝,但秦速亡,为汉所虑。汉初政制,周秦并用,以秦制为主。汉初政策,也是周秦并用。在秦制的基础上如何与文化中国结合,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可汉儒却认为,孔子早就替他们都解决好了,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孔子为汉家立法”,所立之“法”,就是那八个字的“八字宪法”。“祖述尧舜”:这一句,说的就是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以“尧舜”为代表,“祖述”二字,既明确了文化传承,又说明那是一个远祖传说的时代;“宪章文武”:说的则是王朝中国,以“文武”——周文王和武王为代表,而“宪章”则表明“有册有典”。 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就被孔子归纳为这八个字,为历代王朝所奉行,但它并非为王朝中国的君主立宪,而是为文化中国的圣人立宪,故历代王朝,无不活在革命与受命的不确定的更迭中,唯独孔子,两千年来作为文化中国的圣人并驾尧舜。 以两个中国相结合的方式,缔造自家天下,并非汉武帝创举,早有周公为之先驱,但在王朝中国里开孔家店,则其实为第一人,他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后,又加了四个字——“独尊儒术”,从而开启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相结合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孔家店,这店开了两千来年,直至帝制覆灭,王朝不再,才被新文化运动打倒。请注意,是打倒了孔家店,而非打倒孔子,孔家店与孔子,具有不同属性,一属于王朝中国,一属于文化中国。 孔子为汉家立法 汉儒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道的理想。 要在王权之上,树立一个更高的道义原则,使王与道相对二分,就如同基督教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儒家也主张“政归于王,道归于圣”,至董仲舒,始以《春秋》为依据,集汉初儒术之大成,建成以《春秋》为标准的儒家道统观。 在《春秋繁露》里,董仲舒将《春秋》242年之文,归纳为“十指”,以为是“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认定《春秋》大义,要在“正王”,而“正王”必待“素王”出。 “素王”者,帝王之鉴,乃帝王之标准也,舍孔子其谁也?故武帝三问,董仲舒应诏对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亦曰:“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 若以孔子为文化代表,那么董生所言,乃“文化政治化”,以孔子为素王,为汉家立法。同时,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政治文化化”,亦即按照王朝中国的要求,对孔子进行政治改造。 董生学脉,师承公羊高,战国时齐人,后汉戴宏著《公羊传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可见董氏亦属子夏一脉。 子夏之学甚“杂”,吴起、商鞅皆出其门下,虽被《荀子·非十二子》“非”之为“贱儒”,但荀学王霸并用,实亦与之相通,后来,荀子门下出了韩非、李斯,与“子夏之儒”可谓同流。秦汉之际,子夏之学与荀学,同为汉学儒宗。 儒术兼容,至董氏乃大,其于儒家各派,乃至诸子百家,并包而成《春秋繁露》,以儒为主,兼采道、法、阴阳等。 经统计,《春秋繁露》引用“孔子曰”或“孔子之言”,共有二十多次,多见于《论语》之中,也有一些非孔子所言,乃董氏假托孔子言或《公羊》先师所传言,或《公羊》不言“孔子曰”,而其自加之,如此热衷于“孔子曰”,乃以孔子代天立言也。 《春秋繁露》,其言虽杂,要言之,无非两条路线,一是道统路线,以孔子为素王;二是政统路线,王权至上。 素王立法,立于天人古今,“上揆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不仅如此,还口含天宪,宣示天命。故《春秋》之所讥,灾害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正王”——教训王,仅以理性启示不够,还要让灾异来跟随。以《春秋》“正王”,正如君主以刑罚“正民”。灾异似虚无,捉摸不定,把握不住,然而对于人心,尤其是对于不受制约的王者之心,却有神秘的威慑力量。 专制多灾异,此民心之慰藉,亦民心之反抗。专制之下,多有此无可奈何的灾异政治文化,董氏于此乐道,犯了帝王大忌,后来武帝让他以身试法,用灾异吓他一吓,就把他吓回了老家。帝王之于《春秋》“正王”,并非那如影随形的灾异,而是帝王大一统,素王为帝王立法,立的就是大一统。 他指出《春秋》“元始”义,即为一元化。“定于一”,虽为诸子共识,但秦亡后便式微了,董以《春秋》重启。其论,始于《春秋》“奉天法古”,终于孔子“为汉家立法”,而其本旨,则归于大一统。由此宣告了“孔家店”开张。 先以孔子来统一诸子百家,实现思想大一统。再以“素王为帝王立法”,来实现帝王大一统。请注意,不是君主从自身直接“君道同体”,而是在君与道之间,加了一道“素王为帝王立法”程序,使得“君道同体”,必须经由素王立法,此即以素王代表文化中国,帝王代表王朝中国,使两个中国相结合。不以素王为憾,不以君权为高,此董生之所以能超越荀学也。 道统“一元”,董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为道统开端,以孔子为“一元”,表现于政统,是为帝王大一统。为此,董生专著《天道无二》,断然曰:“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然,阴阳为二,何贵何贱?董生曰:阳尊而阴卑。此乃价值判断,非论自然。道统和政统亦为二,未闻孰尊孰卑,但求合而为一,是为“大一统”。合之者,圣王也,故谓之圣王大一统。 董生以《春秋》为政统之法典,其《春秋繁露·玉杯》言之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故屈民以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其落脚点,在“伸君”以“屈民”,为了“大一统”,不惜有损民本主义。 故其《春秋繁露》各篇,皆以政统之君对道统之元,以“元”伸君,“变一为元”,定为纪年之通例,凡“一年”,均作“元年”,王为“元”,使其与圣人合,即为“元者”——圣王。 在君民关系上,君为先,民次之,但又有《灭国上》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汉字形、音、义,皆有妙用,可以假借,使其义相通,如“王”与“往”音同,故以“民之所往”为“王”定义,“君”和“群”形近,故以“不失其群者”为“君”正解。总之,王必须民心所向,君不能脱离群众,这样又回到民本立场。 还有《贵元神》,曰“君为国本,君化若神”;有《立元神》曰“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帝王神圣化,至此已极也。或谓董生,尔既曰圣化,如何又言神化? 然其神化,非授人君以神鬼之术,如方士教始皇帝自隐其形,乃欲为国家立一宗教也。如果说圣化是向历史学习,以上古圣人为榜样,走的是孔子说的“吾从周”一路,那么神化,则是确立宗教信仰,回归殷人上帝传统,走了墨家“天志明鬼”一路。 但汉朝神化,未如其所愿,归入宗教一途,盖因汉武与秦皇多有相似处,两人都生于帝王家,都有雄才大略,都好神仙方术,都想封禅受命,结果,还是走了方士一路。方士引导始皇为所欲为,而董生在神化武帝的后面,留了一个“天谴论”后门。董生“天谴论”,要在王权头上再立个神权,要在政治伦理的基础上确立宗教信仰,就此而言,他有点像墨子。 而墨子,却是个王朝中国的反对派,不承认王权世袭,所以,被王朝排除在外,董生未明乎此,竟然把“天志明鬼”那一套墨家余孽,带到汉家天下里来还魂了,这也许就是董生被“谴”回家的原因吧。汉武未遭“天谴”,他先被天子“谴”了一把。 自大一统以后,王权便无以复加,不受制约的王权,秦已为前车,故应有对王权的制约,制约机制,虽不能被制度化,却可以意识形态化。他从古今关系中发现“素王”,并建立起圣化机制;又从天人关系中发现“天谴”,以之为前提,而有神化机制。以圣化机制,确立帝王大一统,而神化机制中,则含有对王权的制约因素,他将这些因素提出,在王权头上动土,出土“天谴论”,从科学来看,它也许荒谬,可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它却自有其应用的合理性。 道之大原出于天,由天道而人道,形成儒家道统,道统包含儒家精神,而天道则是儒家原则;道统赋予天道政治伦理品格,而天道则给予道统以必然性的力量和自然性特征。奉天法古,是儒家支撑道统的支柱。 天道,是圣化最高原则,又是神化终极追求,几乎所有君主,都会在对天道的追求中企盼君道同体,董生提醒他们,要适可而止,牢记其身份,只是个“天子”,故有《郊礼》曰:“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 天子要以“子礼”事天,有《顺命》曰:“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事父之礼,在人为孝,在天为法。天子与天,此乃“天伦”,非以血缘,而以伦理,“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 天子要法天,有《四时之副》曰:“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王者不可以不知天,天意虽难见也,天道虽难理也,但他已把天道的线条,打理得既简单又清楚,即明阴阳,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以“观天道也”。 董生“子礼”观,对于解构“君道同体”,虽有其积极意义,但落到实处,则有如《郊祭》所言“天子每至岁首,郊祭以享天”,或每遇大事,必郊祭以告天。“天”,作为天子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王权合法性的保护伞,而非制约君主的利剑。 因而,有《郊语》曰,告诫帝王,不可得罪天,“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孔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谓“天谴”,即指当王政不当时,天就会出现某种“灾异”现象以警告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为加强“天谴论”的说服力,他将“灾异”说溯源至《春秋》笔法。 在对答武帝策问文中,他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富于戏剧性的是,灾异没在武帝身上应验,他倒差一点作法自毙。 然而,武帝所以借机惩戒他,说明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一个接受了神化的帝王,骨子里必定留着“天谴论”的阴影,清人赵翼《廿二史杂记》中,专列一条,曰“汉诏多惧词”,由此可见,汉武帝以后的君主,对于“天谴”,或多或少都有些惶恐。 天谴说,非始于董,但影响自董始,且很快就转化了,除诏书多“惧词”外,天谴“灾异”,已转嫁到臣子,遇有灾异,便以三公替罪,轻则免职,重者赐死。这一转化,从天谴说中赦免王权,儒学本位随之也被转换,神本取代人本,君本取代民本。 “素王”不可封 儒学官学化以后,孔子取得了为政统所认可的“素王”地位,但儒者所谓“素王”高于帝王,却未被政统接受,后世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热衷于赐封孔子,即是以此表明帝王至高无上。 “素王”不可封,一“封”便成粪壤,被王权那么一封,品格就低了,不封不低,愈封愈低,本是衡量王的尺度和标准,经此一封,便跌落下来,反而要接受王权主义的尺度来衡量。 汉平帝元始元年,亦即公元元年,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算个什么封号?把圣人孔子封到官本位里去了。不过,这倒符合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身份,也能使他的子孙后裔,从他的封号中,得到封官拜爵的好处。 封号,亦随朝代而变化。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尊孔为“文圣尼父”,北周静帝封之为“邹国公”,至隋唐,隋文帝尊为“先师尼父”,唐高宗则称之为“太师”,武则天改封为“隆道公”,至唐玄宗,始封“文宣王”,而有“素王”本意,后裔嗣爵,袭封文宣公,宋仁宗时,改文宣公为衍圣公,此后,相沿未改。封号变化中,有一事应注意,即夷狄之人尊孔尤甚,如西夏仁宗尊孔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而元成宗则称“大成至圣文宣王”,加了“大成至圣”四字,才将“素王”的本意表达了。 可到了明朝,明世宗仅尊孔为“至圣先师”,把那个“王”字去了,使“素王”转化为帝王师,清世祖又在这基础上加了四个字,尊孔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总之,“夷狄之人”似乎更尊孔,异族入主中原,没有比尊孔更省事,更能利益最大化了。 (刘刚近著《文化的江山》,中信出版社)

微信小程序
微信扫一扫体验
投稿

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扫一扫加关注
评论 返回
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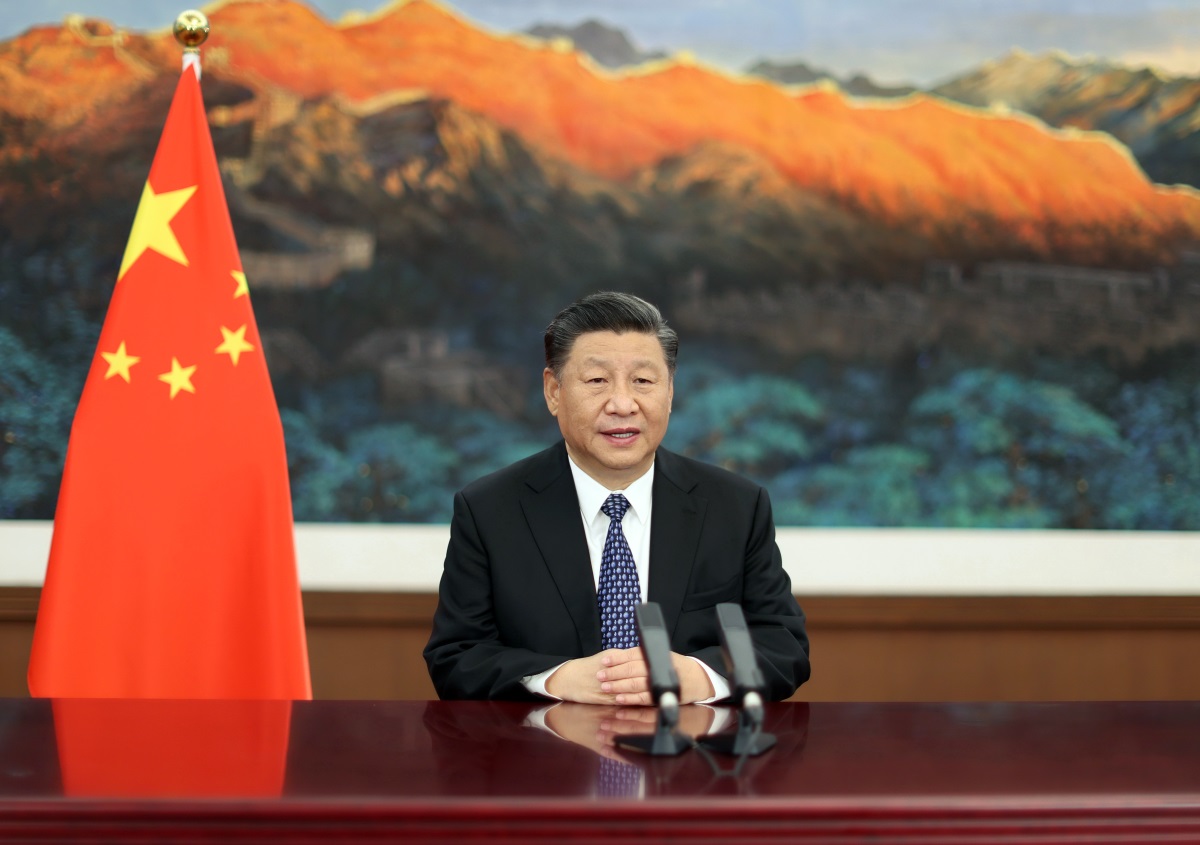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