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阙里,又称阙党,旧指孔子所居之地。围绕阙里之由来、方位及其古今演变,历代多有讨论。黄立振辨析各说后指出,古阙里应在周鲁城北城墙圭门附近,而今孔子故宅前的阙里乃属后起,两者名同实异。(《阙里考略》)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解释其义有三:孔子故里,借指曲阜孔庙,借指儒学。《辞海》谓阙里“旧亦曾用作曲阜的别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阙里已是兼具地理、人文等多重含义于一体的指称。这种多元形象,在清人记述中有着鲜明展现。
皇帝视域中的阙里,是宣扬儒学、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二日,户科给事中郝杰请开经筵,“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得旨:“请开经筵,祀阙里,俱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此举说明,清初统治者甫一立基,便意识到阙里承载的非凡意义,希冀通过阙里祀孔来笼络士人,稳固统治。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世祖为母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将遣祭“先师孔子阙里”列为“恩恤事宜”之一,与致祭历代帝王陵寝并重(《清世祖实录》卷九、卷五三)。
尤能彰显阙里特殊地位者,当属皇帝亲至此地祭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中旬,康熙帝首次南巡回銮,行近曲阜时颁谕:“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旋令臣下议定祭孔仪节。又谕:“朕幸阙里,将行礼讲学,邹鲁圣贤之乡,意必有学问淹通之士”,命从当地选能讲经义者撰写讲章进览。(《康熙起居注》)此处,康熙帝赋予阙里深刻的文化内涵。随后,圣祖亲祭阙里孔庙,讲圣学,瞻圣迹,谒孔林,赐孔裔,成为清代崇礼先师的标志性事件。
雍正帝在位期间,虽未亲至阙里,但也常加提及,时深景慕。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阙里孔庙发生火灾,殿庑俱毁。雍正帝闻奏悚惧不宁,一面遣官驰赴阙里告祭,一面令工部会同地方官作速兴修。嗣后六年多,雍正帝数次督催庙工进度,如称:“阙里文庙工程,关系重大”,“朕于兴修阙里文庙一事,尽诚尽敬”。(《清世宗实录》卷六七、卷七八)至雍正八年工程全部告竣,撰立《重修阙里圣庙碑》,内称:“曲阜庙庭为孔子里宅,毓圣钟灵之地”。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亦有上谕:“阙里为圣人之乡,尤切羮墙之慕”。(《上谕八旗》卷十)雍正帝对阙里孔庙的重视,实质是昭示崇儒理念,以为臣民率则。
乾隆帝绍述父祖之政,曾说:“夫曲阜,圣人宅里。自汉祖以来,谒庙行礼、流传于史册者,指不胜屈”。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上谕以“未登阙里之堂,观车服礼器,心甚歉焉”,确定来年春天幸鲁祭孔。(《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七、卷二九二)自此,乾隆帝凡八次亲祭阙里孔庙。在他看来,“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通过阙里祭孔,自能加深对孔子“穆然而遐思、肃然而起敬”的向慕之情(《阙里盛典·序》),并以此沟通庙墙内外,兼收治统道统。
历经清前期诸帝遣祭或亲祭阙里孔庙,阙里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强化。简言之,它既是孔子生前所居之地,也是后世瞻拜祭孔之所,更是帝王宣扬儒学、示范天下的教化中心。
文人士大夫视域中的阙里,是近接夫子遗风、沾沐先师教泽的神往之地。在传统社会,孔子被尊奉为大成至圣先师,而作为孔子居住地和奉祀地的阙里,自然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域”。有清一代,大量在任或致仕官员、文人学士纷纷往谒阙里,记述了他们的观感体验。
顺治时期,官至广东按察使的王第魁忆述道:“余自总发受经,即于诗书间想象阙里,以不获亲见为歉”。顺治九年四月和十月,他先后两次至阙里谒庙,“渐而望见宫墙,渐而进拜阶下……如有所俯而给焉,如有所仰而承焉”。多年夙愿终得以偿,王第魁不禁感叹:“昔尝于诗书间想象阙里,兹乃于阙里间步趋诗书,余因有独快乎?”这种发乎心底的感受,在士大夫笔下多有所见。辽东广宁人班琏,“自冲龄即受读孔圣书”,每忆其发祥之地便“寤寐难切”。顺治十八年,他赴任山东按察使,公务之暇“获游阙里”。在阙里孔庙,班氏观圣像,陟杏坛,访礼器,询乐所,“如接(孔子)声容,低回不能去”,实为“生平一大快也”。
雍正七年,翰林院掌院学士、通政使司通政使留保接手阙里庙工,自言“顾念迂疏,忝窃科第,叨列清华,祖父以来书香勿坠,皆沐浴先圣之化雨,得以儒臣历受国恩”。如今亲至阙里,“平日梦寐而不得见者,一旦徘徊车服礼器,获睹宫墙美富,又得藉手告厥成功,实不胜庆幸”。曾任山东巡抚的陈世倌,回忆其父礼部尚书陈诜历官四十年,“每以未得一登阙里之堂为憾”。直至康熙五十九年,陈诜致政归里,途径曲阜,“得亲睹圣人之车服礼器,以慰生平愿学之志”。
如果说瞻拜阙里已为文人士大夫所神往,倘能亲与祀事,则更属异数恩荣。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山东按察使司佥事任塾以录科之事按部兖州,适逢阙里上丁常祭。他观察说:“唯我夫子,则每岁春、秋二仲,自京师太学,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声教所通,无不崇祀。而在阙里之庙,则我夫子钟灵之地,车服礼器在焉……视他郡国更为严重”。任塾受衍圣公孔毓圻之请,担任本次主祭,更觉“岂非此生之幸,而凡为学使省,希望而不可得也耶?”遂刻石立碑,以志感念。康熙三十九年,徐炯奉命视学山东,驻于兖州,旋意识到“曲阜,至圣之所发祥也。学使者至兖,例得躬诣阙里,展礼于庙堂”。他于次年五月前往曲阜,适会阙里庙祭,得与衍圣公等人共襄盛典。礼成之后,任氏感称:“今猥以儒臣,叨奉简命,持东国之文衡,拜先圣于阙里”;“而又与于大礼,执爵奉币,登降跪拜于先圣之庭,而展其诚恳,当年提命慨然如可接焉”。此番经历,令任塾“私心徘徊,极自慰幸”,对阙里也益增敬重。(以上引文,见骆承烈汇编《曲阜碑文录》)
相较清帝将阙里看作儒学教化中心,文人士大夫更赋予其某种神圣意蕴。乾隆朝学者、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设问道:“搢绅先生经东国者,辄纡塗,道邹鲁,叩谒宫墙,低佪瞻拜之余,复殷殷谘问,冀益见所未见,而闻所未闻。此岂阙里规模果殊于他郡邑哉?”(《劻仪纠谬集·序》)他给出的解释是,此地乃圣人故里,车服礼乐之余蕴绵延不绝。文人士大夫亲至阙里圣域,便如近接孔子本人,沾沐先师教泽,可以坚其自省躬修之念,增其向往服行之心。
基层官员和民众视域中的阙里,带有多面复杂意象。康熙《曲阜县志》载:“曲邑大都,重礼教,崇信义,有先王之遗风”。又称:“曲阜实今古奥区,神皋帝王之都会,大圣仁贤之闾里,其他砥行立名,绥猷树勋,史不绝书,天下曾不得望尘而争衡焉”。孔继汾则把阙里与曲阜等称,描述说:“阙里为古帝王都会,山川灵秀,圣哲迭兴,沐教泽而被遗风者,其俗固宜与他处异”;“阙里为六艺之宗,天下之大文备焉”。(《阙里文献考》卷二九、卷三二)类似文字不胜枚举,意在凸显阙里为帝王圣贤荟萃之地,故而德泽深厚,仪章不泯。
阙里的神圣光环,为其博得了崇隆声誉,却也难掩隐藏其后的不同声音。清初几十年间,曲阜一带“地瘠民贫”、“土寇窃发”、“军役烦兴”,朝廷免役恩例置若弁髦。当地民众“奔命弗暇”,并没有亲炙阙里之恩泽庇荫。(骆承烈汇编《曲阜碑文录》)其后,尽管清廷屡免曲阜差徭,但“凡部使监司有事于东省,南北过客假道于兖城,无不趋谒阙里者,往来迎送,冠盖络绎,名虽僻左,实则冲繁”。巨额的接待支出,给当地造成较大财政压力。百姓受此之累,“左支右绌,安得不困?”(乾隆《兖州府志》卷十七)这些描述,一定程度上映衬出地方民众对阙里的复杂感受,而这恰恰可能被清代皇帝与文人士大夫所忽视。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08日 1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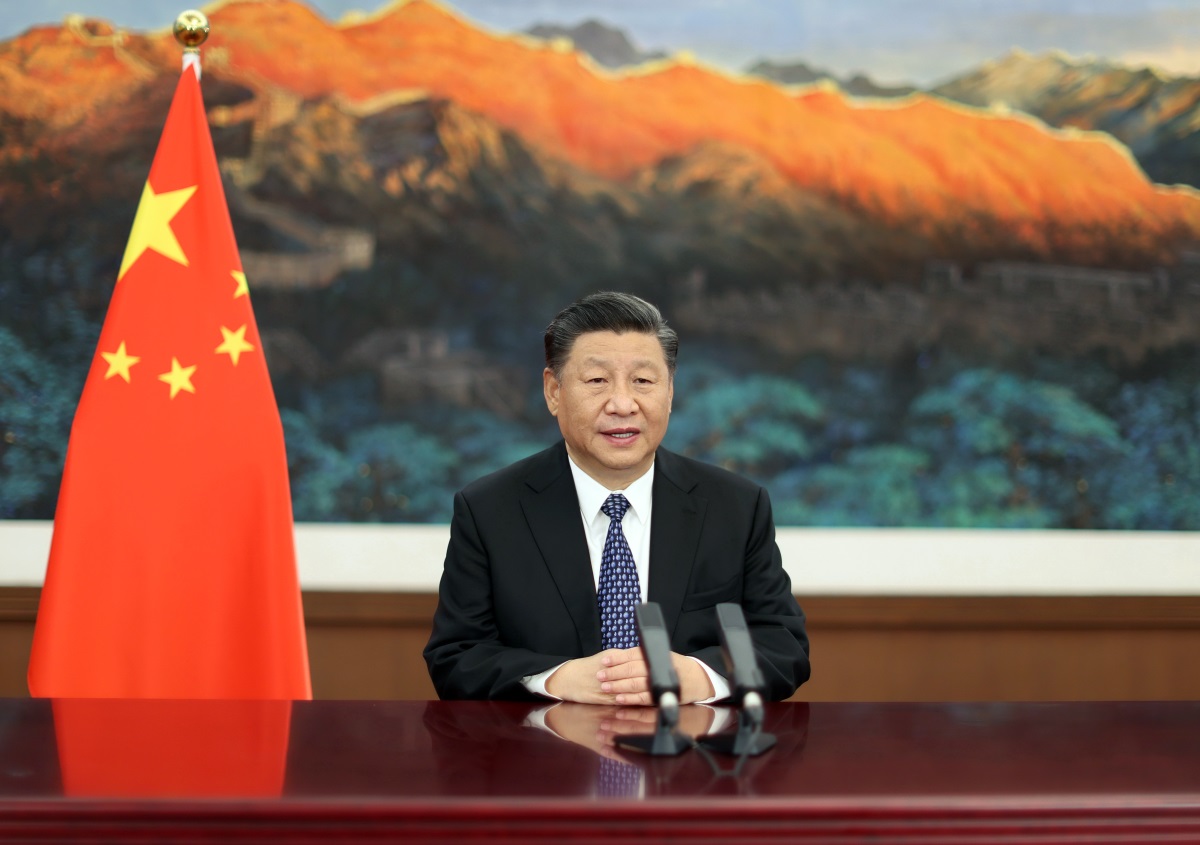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